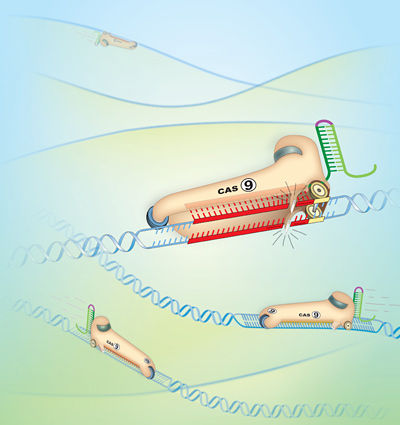几年前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结论如下:
纽约大学菲利普-泰尔诺博士指出,如果冲水时马桶盖打开,马桶内的瞬间气旋最高可以将病菌或微生物带到6米高的空中,并悬浮在空气中长达几小时,进而落在墙壁和牙刷、漱口杯、毛巾上。现在大部分家庭中,如厕、洗漱、淋浴都在卫生间里进行,牙刷、漱口杯、毛巾等与马桶共处一室,自然很容易受到细菌污染。因此,应养成冲水时盖上马桶盖的习惯。
对此研究的全面解读 :从两篇2012年发布的医学综述里引用的众多论文来看,抽水产生的气旋与微生物的传播确实有着一定的关联,冲水时盖上马桶盖这个习惯也值得提倡[1][2]。
不过,这些研究在社交平台上传播时,研究中很多关键的信息——哪些微生物可能通过这个途径进行传播?这些微生物传播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传播扩散后的微生物对人体有多少潜在的危害?——被忽略,只压缩成一个简单结论,而且增加了“马桶内的瞬间气旋最高可以将病菌或微生物带到6米高的空中,并悬浮在空气中长达几小时”这些研究中没有提及的细节。
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有条件扶摇而上
只有那些天赋异禀的微生物才能借马桶气旋的东风。200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马桶中培养的沙门氏菌能够聚集成一种叫“生物膜”的结构,牢牢地植根于下水道中。由于有这么一个细菌的“储备”,在实验结束的12天后,人们依旧能在马桶中发现它们的身影[3]。这也增大了它们借抽水气旋传播的可能。而另一些微生物无力往深处发展,就将目光投向了相反的方向。早在1980年,科学家们就发现那些细胞内含有较多脂质的细菌更容易富集在水体的表面[4]。倘若有气旋能将水中的微生物带起,它们将是微生物中的急先锋。
不过,这些微生物本身的特性并不足以让它们从马桶中传播到空气里,气旋威力的大小也决定了传播范围的大小。有意思的是,至今为止人们对这种气旋的物理特性还是一知半解,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种气旋会随着马桶类型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由于实验中采取的微生物不同,传播范围也各有所异(实验马桶多为“虹吸式”)。大肠杆菌会在冲水后的2个小时内集中分布在以马桶为中心直径约1米的范围内[5],沙门氏菌能在30分钟内扩散到同样的范围[3],而梭状芽孢杆菌则主要在60分钟内聚集在马桶坐圈到马桶上25厘米的范围内[1]。
在一些观察较久的实验中,微生物能够以极低的浓度扩散到整个卫生间(墙上的培养皿只有20%有细菌生长,单个培养皿中最多长了5个菌落;浴缸内的培养皿只有5%有细菌生长,不过单个培养皿中最多长了大于100个菌落),这也与含有微生物的液滴与空气的混合、扩散有关。
不过在这些研究中,并没有微生物扩散到6米高度(作者吐槽:要找一个房高超过6米的卫生间也挺难的……)的记录。至于这些微生物能在空气中停留多久,更是没有定论。
警惕但无需恐慌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通过马桶气旋传播的微生物可能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影响。结核杆菌的脂质较多,容易在马桶残水的上层积聚。当人的肠胃道感染结核杆菌后会引起腹泻,造成其再次传播。不过据估计,这只占总体感染病例的5%不到[6]。
另一种可能通过马桶气旋传播的微生物则家喻户晓——SARS 病毒。一项关于2003年香港淘大花园SARS爆发的报告推测可能是最初发病的SARS病人的排泄物通过楼层里的下水道和排气扇迅速扩散,造成了整栋楼内SARS的爆发[7]。
不过这些或是极端情况,或是尚未证实的研究猜测,日常生活中由马桶气旋带来的潜在危害可能没有那么大。另外,无论哪一种微生物想要致病都需要有一定的“致病剂量”。在上文提到的实验中,研究人员都将微生物与粪便或培养液均匀混合成悬浮液而进行测试,这种情况自然有助于微生物的传播。在实际生活中,只有腹泻或呕吐接近实验中的条件。换言之,正常情况下的便溺只会更限制微生物的传播,空气中的浓度也会更低。
不过,空气中通过气旋悬浮起来的微生物浓度能依据种类的不同而有上百倍的差距,因此马桶气旋带出的具体微生物的是否能够致病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马桶“进化”的利与弊
【图1:3种不同的马桶类型。左上为最初的冲水马桶,右上为无马桶盖的“无框式”马桶。下为最常见的“虹吸式”马桶以及其工作原理 (图片来自网络)。】
最早的冲水马桶 (图1左上)依靠水流下冲的重力顶开底部的阀门进行冲洗,由于其下部的管道结构较为简单,产生的气流也比较大,现多已淘汰。
在美国,“虹吸式”马桶(图1下)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替代第一类冲水马桶成为家庭马桶,目前国内家庭马桶也多使用“虹吸式”。当设计师们将排水口改成了“虹吸式”后 ,同样用于冲洗的水流带起的微生物大约只有前者的1/14 [8]。
最新的“无框式”马桶(图1右上)在公共场所(比如学校、医院)中更为多见。这种马桶取消了顶盖的设计,抬高了坐圈的高度,以期让脏垢无处藏身,殊不知藏匿的微生物是少了,气旋溅起的液体却变多了 [1]。与“无框式”马桶相比,“虹吸式”马桶冲水时产生的气旋更小。
【图2:“虹吸式”马桶(A)与“无框式”马桶(B)溅水程度的比较 [1]。】
最后,还有一些其他措施可以减少通过气旋传播的微生物。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在冲水时盖上马桶盖了。这项简单的方法能够将飞溅的微生物含量减少到不盖盖子时的1/12 [1]。此外,定期用消毒水清洗马桶和水箱也能够限制马桶内微生物的残留。
结论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有些微生物更容易在马桶周边积聚。马桶冲水时的气旋的确能够造成微生物的传播。虽然这些微生物的传播范围、时长尚且未知,但在冲马桶时盖上马桶盖,定期用消毒水清理马桶和水箱,确实能够帮我们减少潜在的健康危险。
参考资料:
[1] E.L. Best et al. 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80 (2012) 1-5
[2] D.L. Johnson et al. 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 (2012) xxx 1-5
[3] Barker J, Jones MV. The potential spread of infection caused by aerosol contamination of surfaces after flushing a domestic toilet. J Appl Microbiol 2005;99:339-47
[4] Hejkal TW, Larock PA, Winchester JW. Water-to-air fractionation of bacteria.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80;39:335-8
[5] Gerba CP, Wallis C, Melnick JL. Microbiological hazards of household toilets: droplet production and the fate of residual organisms. Appl Microbiol 1975;30: 229-37
[6] Sheer TA, Coyle WJ. Gastrointestinal tuberculosis. Curr Gastroenterol Rep 2003; 5:273-8.
[7]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Unit Department of Health. Outbreak of 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at Amoy Gardens, Kowloon Bay, Hong Kong: main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 March 29, 2011. Available (from:http://www.info.gov.hk/info/SARS/pdf/amoy_e.pdf. Accessed Mart 29, 2010.)
[8] Bound WH, Atkinson RI. Bacterial aerosol from water closets: a comparison of two types of pan and two types of cover. Lancet 1966;1:1369-70